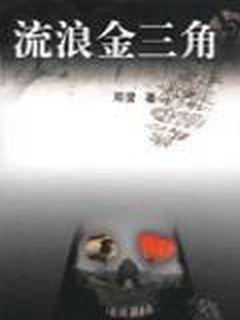- [ 免费 ] 第一章:《历史的禁区》 ...
- [ 免费 ] 第一章:历史的禁区
- [ 免费 ] 第二章:《走进金三角》 ...
- [ 免费 ] 第三章:《潘多拉魔盒》 ...
- [ 免费 ] 第四章:《铤而走险》 ...
- [ 免费 ] 第五章:《背水一战》 ...
- [ 免费 ] 第六章:土司招亲
- [ 免费 ] 第七章:封疆大吏
- [ 免费 ] 第八章:“反攻云南!” ...
- [ 免费 ] 第九章:掸邦风云
- [ 免费 ] 第十章:帝国神话
- [ 免费 ] 第十一章:“旱季风暴” ...
- [ 免费 ] 第十二章:谲波诡云
- [ 免费 ] 第十三章:大撤台
- [ 免费 ] 第十四章:《兵燹》
- [ 免费 ] 第十五章:刀锋相向
- [ 免费 ] 第十六章:危机四伏
- [ 免费 ] 第十七章:仰光枪声
- [ 免费 ] 第十八章:兵车南行
- [ 免费 ] 第十九章:“湄公河之春” ...
- [ 免费 ] 第二十章:罂粟王国
- [ 免费 ] 第二十一章:末路英雄 ...
- [ 免费 ] 第二十二章:《龙蛇争霸》 ...
- [ 免费 ] 第二十三章:坤沙出逃 ...
- [ 免费 ] 第二十四章:神秘满星叠 ...
- [ 免费 ] 第二十五章:青春似血 ...
- [ 免费 ] 第二十六章:走向深渊 ...
- [ 免费 ] 第二十七章:灵与肉
- [ 免费 ] 第二十八章:知青火并 ...
- [ 免费 ] 第二十九章:理想之光 ...
- [ 免费 ] 第三十章:朝廷招安
- [ 免费 ] 第三十一章:荡寇志
- [ 免费 ] 第三十二章:灰飞烟灭 ...
- [ 免费 ] 第三十三章:〈金三角之魂〉 ...
杏书首页 我的书架 A-AA+ 去发书评 收藏 书签 手机
繁
第三十三章:〈金三角之魂〉
2024-4-24 20:40
1
金三角,美丽的金三角!
如果不是贫困、疾病、战争、毒品、暴力和罪恶困扰着这片美丽如画的原始土地,它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具开发价值的旅游胜地。那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令人眼花缭乱的珍禽异兽,雄伟而奇异的山川河谷,还有神秘动人的风土人情、民族部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都是人类世界不可多得的最后遗产……
我从美斯乐前往孟萨采访途中,在一处地名叫做中寨的地方,时值下午,太阳已经偏西,突然一片云彩涌来将阳光遮挡。我抬头一看,天空如洗,哪来什么白云?分明是成千上万的鹭鸶和白鹤在天空快乐地翱翔。我是城市人,打我记事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数量如此之多的白鸟,它们像圣洁的雪片,像传说中上帝的天使,像我小时候读过的童话故事中美丽的精灵在天上翩翩起舞,它们不停洒下细碎而快乐的叫声填满我的心房。太阳斜斜地透下来,天空因了它们而变得无比生动,无比美妙,我像走进一个纯洁的梦境,走进一个真正充满高尚一尘不染的童话世界。我流下眼泪,不是为悲痛而是为美丽而哭泣,是为我们这个世界至今还保留的一片美好圣境,一块能让我们心灵安静憩息的神圣净土而感动得热泪滚滚。
朋友说:这是金三角有名的鸟国,像这样规模的天然鸟国还有几处。
哦,鸟儿,美丽的鸟儿,你们快乐地飞翔吧,但愿人类的罪恶不要干扰你们最后的舞蹈。我在心中默默祝愿。
但是一年多后我接到朋友来信,他说由于修公路发生山火,我们到过的那个鸟国已经不复存在。一连数日,我伤心难眠。
在金三角,我有幸见过一次野象群,那是在马鹿塘采访的日子,一天清晨,我偶尔发现村子对面的山坡上有许多移动的幢幢黑影,我怀疑自己看差了眼,连忙取出望远镜来。我的天!那是一群大大小小的亚洲野象,约有十几头,正甩着鼻子和尾巴,悠然自得地从树林里走出来,绕过村子边缘,这仿佛是一种古老的约定,与人类友好相处,互不侵犯,所以身躯庞大的它们丝毫没有侵犯人类的意思,又慢慢走进对面的山箐,消失在黑黝黝的树林世界里。
我内心感动无以复加。是谁背信弃义,撕毁古老约定,疯狂侵略动物家园,大肆滥杀珍禽异兽?是我们人类!是罪恶的人类!在金三角,尚存大约十万平方公里热带雨林无人区,这是地球上仅存不多的动植物基因宝库之一。但是我从有关方面获悉,近年来由于毒品犯罪呈现内敛之势,许多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当地民族“罂粟部落”都向无人区深处迁移,他们毁林开荒,烧山烧林,日趋破坏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更由于国际社会对毒品犯罪打击力度加大,一些毒贩将走私犯罪的贪婪目光又盯上野生动物,于是数量稀少的亚洲虎、亚洲野象、金丝猴、马来熊、黑猩猩、白孔雀等等成为罪恶枪口的牺牲品。仅中国云南海关1999年多次查获从金三角偷运入境的珍贵动物皮毛数以千计……
惊心动魄!罪大恶极!
2
金三角,苦难的金三角!
自从1950年国民党军队闯入这片原始而寂寞的土地,如同一个古老的魔盒被上帝之手打开,没有飞出象征吉祥幸福的和平鸽,也没有象征财富的金羊毛和金剪子,而是站起一个面目狰狞的黑色妖魔——毒品王国。
自此金三角年年战争,苦难重重,战争和毒品的烟雾笼罩在这片美丽土地的上空再也没有消散。罪恶的痕迹好像一道道丑恶的疮疤涂抹在金三角大地上,就像那些原本纯净的心灵被打下无数丑陋的烙印。我不禁要问:金三角,这个人类的世纪噩梦,你究竟还要狰狞多久?
一个掸邦头人对我说:如果我们不种大烟,我们拿什么东西换回我们需要的盐巴、酒精、布匹、煤油、火药、子弹、农具、百货和日用品呢?那时候连马帮也不会进山来,因为他们只会空手而归。
在另外一个比较靠近公路的寨子,本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投入资金帮助当地人开发和种植经济类作物,以替代罂粟的经济效益。第一年种植草莓,建了塑料大棚,实验结果很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山坡太陡,气温太高,旱季太干,雨季又太多雨水,大面积推广注定不能取得成功。
第二年改种大白菜,一年两季,获得丰收。问题是丰收的大白菜堆积如山,没有公路,靠什么驮运?如果靠人背马驮,再经公路铁路水路运进城市,大白菜就变成黄金价。所以大白菜只好全都烂在山里,变成蚊虫飞舞的生态污染源。
后来尝试种植甘蔗。泰国、老挝、缅甸相继同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合同,在金三角以及周边新建若干糖厂,以引导当地居民搞替代种植,增加经济效益。许多原来种植鸦片的坝子和交通方便的地方,碧绿的甘蔗林取代了姹紫嫣红的罂粟花,一车车滚滚而来的白糖以及甘蔗副产品酒精、化肥等等取代了黑糊糊的鸦片和海洛因。联合国有关组织1998年发布公告说,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大约缩减五分之一,是近十年中毒品种植面积最低的一年。
种植甘蔗毕竟只是有效努力之一,一个困难的前提是,运输沉甸甸的甘蔗需要公路,需要交通条件,所以这项改革措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难以在金三角更加广大的山区腹地推广。[奇书网-wWw.QiSuu.cOm]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缉毒官员说:由于高科技的引入,毒品犯罪更加隐蔽化,各种新型类别的毒品层出不穷。同五六十年代庞大的鸦片走私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就是同七八十年代的粉状海洛因相比,也已经今非昔比。比如冰毒、药水、药丸,毒贩将毒品精制成各种体积小重量轻的成品,从前需要一支庞大的马帮才能驮运的沉重鸦片,如今变成体积小重量轻的药丸,一匹马就能轻易带走。仅1998年底泰国政府发布缉毒通告,在金三角南部的泰缅边境一次就缴获毒品(药丸)高达二百三十万粒!
世纪之交的公元2000年,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传来,据美国国务院公布数字,1999年金三角生产鸦片较上年减少百分之六十二,呈递减趋势。而一个从前并不生产鸦片的穆斯林国家阿富汗却异军突起,首次超过金三角成为世界上新的鸦片王国。
毒品的魔影没有远去,它仍在威胁整个人类,但是人类社会毕竟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毒品的未来,走向文明的大同世界。我相信金三角也将缓慢而艰难地走出历史和毒品的阴影,只是这个过程充满艰辛,充满流血冲突和无法避免的牺牲……
3
公元1992年,一条新闻传遍全世界:金三角汉人自卫队也就是前国民党残军,终于向泰国政府交出全部作战武器。至此,从1950年李国辉兵败大陆算起,这支创造金三角神话的汉人军队终于正式解体,变成真正的和平居民,而金三角泰国境内多达近百座的汉人难民村不再拥有合法武装,成为名副其实的和平村。
如今的美斯乐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宁静的难民村。
远远望去,群山环抱之中,黛色树林如波浪起伏,一碧如洗的蓝天之下,一座金碧辉煌的佛教寺院如极乐世界高高矗立。这座佛寺为当今泰王九世的母亲,也就是皇太后亲自捐赠给美斯乐居民的,以示皇恩浩荡,如沐春风。佛教乃泰国国教,因此这个举动也可以看做仁慈的皇室对于这些归顺政府的汉人难民一种特殊恩典,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寓意不可谓不深长。你们既然归顺政府,就不能再信仰什么三民主义,你们必须皈依佛教。归顺不仅要归身,还要皈心。所以如今这座佛寺就成了难民村的精神和政治象征,每逢政府规定的宗教节日,佛寺里人头攒动,一派香火旺盛的可喜景象。
1992年之后,美斯乐逐渐向外界开放,准确说是搞活旅游经济,利用金三角的名声赚钱。于是在那座圆弧形巨大金佛塔俯瞰之下,我曾经独自下榻的美斯乐丽所,从前杀气腾腾的反共抗俄训练班旧址变成一座花团锦簇的山林公园,公园四周修起宽敞的回廊,有许多摊点出售旅游纪念品和当地土产。我有时爱到公园徜徉,因为是雨季,少有观光客,所以我这个外人很快就与摊主熟悉了。摊主无一例外都是女人,有老太太,抱孩子的大嫂,也有花季少女,绝没有一个男人,连一个白发或者秃头的老男人也没有。我从这里经过她们便招呼我,拉我看这看那,总之很热情执著地劝我买她们的东西。
她们的货物相当单调,基本上千篇一律,没有什么特产,说明此地旅游经济刚刚起步。我看见除茶叶、干菌和木耳是当地货外,一些标明玉石但天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石头(当地不产玉),其余货物多为大陆舶来品,有药品、食品、百货等等,如红花油、风油精、娃哈哈、男宝女宝之类,居然还有一朵来自峨嵋山的干灵芝!我指着灵芝问她们,这是从峨嵋山来的吗?摊主是个抱孩子的大嫂,三十多岁年纪,她向我保证说是从峨嵋山进的货。我笑了,说:“你去过峨嵋山吗?告诉你,峨嵋山早就没有灵芝了。”大嫂就装出生气的样子骂道:“你这个台湾鬼佬!这朵灵芝就卖给你家了,你家不买就不放你走人!”
金三角民风淳朴,一人做生意,别人也不抢道,都围在一起做说客。她们管台湾人叫“台湾佬”,香港人叫“香港仔”,日本人叫“小鬼子”,惟独对大陆人没有称呼,因为大陆游客基本上是个空白。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台湾佬?”她们一伙女人就嘻嘻哈哈地笑,说:“你家不是台湾佬?嘿,看你家的衣服,还想骗人!”那天我穿了一件在台湾桃园机场买的T恤衫,上面印有台湾机场字样,所以她们便认定我是台湾佬无疑。她们对台湾佬的好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金三角,许多难民村随处可见各种牌匾,上书某某学校、某某道路、某某建筑或者某某公共场所,为台湾某某捐建字样。连清莱到美斯乐的山区公路都是由台湾慈善公会捐建的。另外台湾每年都要拨给难民村一定数量的名额,选拔学习成绩优秀的中学生到台湾免费读大学,这也是汉人后代走出大山,走向文明社会的一个机会。
我说:“你们错了,我真的不是台湾佬,我从大陆来的。”她们停止说笑,个个都很惊奇,互相看看,脸上写满疑问。我就掏出护照让她们看,她们叽叽喳喳地传看,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识汉字。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大约识一点汉字,但是她好像不大认识简体汉字,偏着头看了半天,然后不服气地说:“你家从大陆来?大陆哪个省,哪个县?”我知道她们百分之九十以上祖籍都是云南人,就存心跟她们开玩笑说:“我从云南来。云南省成都市。”
她们全体发出“啊嘎——”一阵惊叫,然后惊讶和兴奋之情就久久地停留在脸上。几个人同时争着告诉我,她们也是大陆人,老家都在云南。我发现她们对“云南成都”的错误毫无察觉,就装作对她们来历一无所知,故意问她们都是云南什么地方人?哪个地区,哪个县?回去过没有?她们显出茫然的样子,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回答她们应该是云南什么地区,什么县,哪个村子人氏。当然更没有人回过老家。
我装出不相信的样子,说你们都是假云南人,连云南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说话口音也不对头。那个年轻女孩子委屈地分辩说,“那是我爷爷的老家,连我父亲都没有回去过。但是你家听听,我们说的可都是真正的云南话啊。”我笑着纠正说,“你们说的哪里是云南话,是金三角话。”她们全都不服气,齐声说:“你家说给我们听听,哪样才是真正的云南话?”
准确说,金三角汉话比较接近滇西话,它实在是一种很好听的,发音软软的(云南话音调较硬),明显带有混杂口音的华侨语言。记得我在边疆当知青,农场人来自天南海北,所以农场出生的下一代就讲一种不同于任何云南地方话的“农场话”。我认为金三角的汉话有一点像农场话,也与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华语相似,没有云南地方腔,却有云南调,因此更像一种云南普通话。因为我通常与她们讲的是普通话,所以她们并没有真正听过我的口音,现在她们一齐噤了声,眼巴巴地望着我,那种迫切表情,很像一群孩子安静地等待大人讲故事。
我清清喉咙,用标准的四川话(我不会说云南话)念了一段大观楼长联,又跟她们讲了一个成都浣花溪和杜甫草堂的美丽传说。我看见她们的眼睛一个个瞪得灯泡一样大,都没有了声气,仿佛停止了呼吸。等我讲完之后,静了好一阵,才有人呼出气来。她们不断“啊嘎——”、“阿嘎——”地发出由衷惊叹,我看见她们脸上有了毫不掩饰的佩服,乱纷纷赞美道:“哇,真好听,你家才是真正的云南话!原来云南话就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却因自己这个没有恶意的小把戏感到难过,感到自责,心中漾起一种没来由的悲哀。我相信这群善良的同胞分不清家乡话并不是她们的错,她们原本是一叶远离大陆的扁舟,一片脱离大树的落叶,任凭命运的风暴刮向天涯海角。她们的后代,以至于后代的后代会不会说家乡话又有什么关系呢?
哦,我的没有根的同胞啊!
4
有人告诉我,金三角有几多,孤儿寡母多,残废男人多,公墓乱坟野狗多,等等。我深入金三角山区数百公里,沿途采访数十座村寨,所见所闻果然不谬。
连年战乱,生灵涂炭,人命如蚁蝼,如衰草,硝烟连天哭声恸,一将功成万骨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这样一幅“千村万落生荆杞”的悲惨景象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延续了两千年,然后又在金三角土地上继续了五十年。男人打仗卖命,有人收回白骨,有的人什么也没有盼回,就像渔船一去不复返,未亡人只好拖着孤儿寡母,艰难地把日子过下去。我在许多地方,接触两代甚至三代寡妇同堂的家庭并不鲜见。
战死的人,哪怕粉身碎骨,只找到一绺头发,一根白骨,也算有个交代。所以打仗人有个规矩,就是把战死者的一件东西,哪怕一片衣服碎布带回来安葬。因此作为汉人部落顽强存在的标志,就是村外山头上那些醒目而庞大的坟场。
我曾在“美斯乐之父”段希文将军豪华气派的大型墓地前流连,我也曾仔细考察雷雨田将军虚席以待的显赫归宿之地,还有许多军长师长的坟墓,这些墓地不仅如愿以偿地留住了主人生前的地位、权势和无限风光,而且也生动形象地昭示部下,即使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长官也比士兵过得好。
作为鲜明对比,那些长眠山头的士兵土坟就不大美观,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塌的塌,陷的陷,有的地方挤作一团,有的地方又稀稀疏疏,由于无人管理荒草疯长,连那些墓碑也都歪歪倒倒。有的还有一块石头墓碑,上面刻几个汉字,注名生辰年月,姓氏籍贯等等,有的干脆没有墓碑,也没有名字,也许只有他们活着的亲人记得他们的最后归宿。
这样豪华与简陋,显赫与无名的坟场墓地在每一个金三角难民村比比皆是,至于总数到底有多少,几百处还是几千处,总之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它们的确切数目。我认为即使弄明白也没有太大意义,活着的人还没有脱离苦海,你就算把死人弄明白又能怎么样呢?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念头在乱坟间到处游荡的。
当时有向导小米陪同,但是他是个相信风水的人,对我坚持要去坟地考察很有意见,认为这是一个将给他的年轻人生带来晦气和背运的倒霉建议,他想不通我为什么偏偏喜欢上那种地方,而一个大活人上那种地方乱逛有什么意义?难道准备把自己跟他们埋在一起不(奇*书*网-整*理*提*供)成?所以他就一个人远远躲在公路上等我。我这人不大信鬼神,所以也就不怕晦气,我之所以坚持要来坟地,是因为我想亲眼看一看,那些长眠地下的原国民党残军官兵都保留什么样的心情。
我看见军官依旧扬眉吐气飞扬跋扈,士兵窝窝囊囊愁眉苦脸,他们即使到了地下也不能混为一谈。我在泰缅边境一座著名的桂河大桥(二十世纪经典战争片《桂河大桥》即以此为题材)盟军阵亡者墓地,看见数以千计的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阵亡官兵的墓碑,他们从上校到列兵,每人占有相同面积(大约一个平方)墓地,一块完全相同的铸铜墓碑,上面铭刻各人的国籍、姓名、出生年月、军队番号和军阶职务。那是一种和谐地体现西方人即使到天国也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不搞特权,你在人间握有再大权力,享有再崇高威望,即使你是万人之尊的将军,都被时光无情地留在了过去。到了天国,站在上帝面前的你我他同样一无所有,只剩一颗被剥得光溜溜的灵魂。
硝烟终于散尽,狼烟远去,昔日的战场和杀戮之地,现在正在发生改变,金三角正在恢复宁静。我仿佛看见那些长眠地下的人们,一双双饱含期待的目光穿越岁月隧道和历史风雨,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与我视线相遇。他们都是中国人,龙的子孙,永远躺在异国土地上,他们的后代在金三角继续生长繁衍,他们是根,他们的后代是树干和枝叶,这就很像移栽或者嫁接树木,最终必将结出另一种果实。我觉得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物种进化和不被淘汰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适应环境。
树根们在地下沉默。
我觉得他们似乎还在期待什么,或者他们还想表达什么,但是坟地一片沉寂。我在广大无边的静谧中遨游,似觉冥冥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它不是声音,也不是文字、图像或者形体,而是一种气,一种感应,一种磁场。它不是物质的,因为物质无法穿越两个世界的界限,所以它一定是非物质的,类似意念、精气、灵魂之类,这些神秘的东西包围我,而我完全是凭着第六感官,也就是灵感才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我开始进入一个非物质世界!
我感到自己不可思议。我想我这个自称无神论者的人可能疯了,至少精神出了毛病,因为坟地上空无一人,我怎么可能与死者对话呢?或者说就是死人发出什么密码信息,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静谧像渐渐凝固的冰块,寒气压迫着我的神经,我感觉一个东西离我越来越近,我无法看见它,但是我分明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像你觉得身后有人,一回头却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一样。你没有看见什么并不等于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我的新发现,我总觉得自己快要接近一个东西,伸手就要捉住它,然而它总是像空气和水一样从我手缝中溜掉,差之毫厘,失之交臂。于是我苦恼万分,灵魂苦苦挣扎。意念之手无边无际,若有若无,佛说,大道如天,大化无形,我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这时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脚步不是来自天空大地,而是来自我的内心深处!
我疑惑地放眼四顾,一轮辉煌的夕阳正像一艘庞大的航空母舰慢慢燃烧西沉,在我身后,金三角重重叠叠的山峦在夕阳余辉中灿烂燃烧。我看见北方的大山峡谷之中,一条汹涌澎湃的著名大河在岁月激流中渐渐冷却凝固,它的形状像一条中国的龙图腾,龙的上半段在中国,叫澜沧江,下半段横贯南部亚洲,名字叫湄公河。而我脚下,就是那些不幸灵魂的栖息之地,远远的山坡有条通往美斯乐的空无一人的公路。
座南面北!面北……
一瞬间,我忽然大彻大悟,灵魂出窍,夏雪冬雷,石破天惊。我的全部灵魂与那个游荡的历史意念迎面相撞,就像宇宙飞船和太空舱对接。
我轰然爆炸!
请跟我来读懂那群流浪的中国人吧!他们长眠在地下,这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无论他们生前做过什么,当兵打仗,离乡背井,抗日战争,反攻大陆,走私贩毒,龙蛇争霸,你争我斗,效忠朝廷,他们死后都亲热地拥挤在一起,背向金三角,背向异域和陌生的印度洋,他们与我目光交织,那是何等热切和期盼的生动目光!于是我明白了,在我脚下这片土地上,一群漂泊无根的中国人,他们永远面向北方,那是他们共同的祖国和家乡,是他们魂灵和精神向往的归宿之地!
哦,北方!我的永远的……北方啊!
我想起一部曾经感动无数中国观众的日本影片《望乡》。妓女葬身南洋,但是她们全部背向北方,因为她们日思夜想的日本国已经抛弃她们。而这群离乡背井的中国人,他们却个个面向祖国,至死不渝!
1998年秋天,我在金三角看到的这一幕不是电影,不是艺术造型而是一个令我肝胆俱裂的真实场面,数以千百计的坟墓,一律整齐地面向北方,面向祖国!这是一个何等惊天地恸鬼神的感人场面啊!后来我陆续考察段希文墓,雷雨田墓,各处汉人难民村墓地,居然全部惊人地一模一样,无一例外者!他们全都面向祖国和家乡,长跪不起!
这时我的眼泪再次汹涌而出,泪洒滂沱。是的,人可以死,尸体可以腐烂,墓碑可以剥落,名字也可以遗忘,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与祖先血脉相连,敬畏永存。有这分思念,这种姿势,这种永不改变的炎黄子孙对故国故土的感激之情就足够了,他们长眠金三角,但他们永远是中国人。
我伏身而跪,向死者,向我魂牵梦萦的同胞之魂,重重磕了三个头。
5
小米见我走上公路神情有些恍惚,就紧张地问我:“看见什么了吗?”
我说:“他们……回家了。”
小米说:“他们是谁?”
我改口说:“哦……应该是我们,走吧。”
一周之后,我返回中国大陆。
1998年10月1日—1999年7月5日初稿
2000年5月 四稿改定 7119509
后 记
当我已经从金三角返回国内,一些朋友陆续得知我独自深入金三角的消息,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责备我:你为什么要到那样的地方去?你不怕死吗?
朋友的关心令我感动。我肯定是怕死的,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生活那么美好,人生那么短暂,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对未来还有那么多期待,我怎么愿意去死呢?如果我不幸死了,我到金三角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从来不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甚至算不上一个勇敢的人。我天生胆子小,有恐高症,晕血症,惧怕开刀,从不敢玩“蹦极”、“过山车”之类勇敢者游戏。如果乘飞机在高空遇强气流,每次我都会因为恐惧而紧张得身体颤抖冷汗涔涔,我不能想象如果飞机掉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模样。同样的恐惧还发生在几次身体不适时,我疑神疑鬼觉得自己患上什么不治之症,绝望得好像判了死刑。
小时候我常问自己,如果你上了战场会是个好士兵吗?如果你被敌人抓住严刑拷打能挺得住吗?上述问题我从来不敢深想,因为答案藏在心里,它分明使得我心情沮丧,对自己评价失去信心。
问题是1998年夏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进入金三角采访,我对危险完全不屑一顾,勇往直前,藐视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这不是说我变得勇敢起来,而是因为我浑身燃烧着激情、向往和冲动。
当满星叠发生枪战打死好几个人时,当地朋友都阻拦我前往,我并不是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危险,死亡实在是个很短暂的过程,一旦发生便不可更改。但是我还是被巨大的好奇心、职业的采访欲望和对写作的热爱所驱使,对我来说,那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好比飞蛾扑火,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所畏惧。我对朋友讲,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就是丢掉性命我也决不后悔。我奇怪自己作出这个决定很冷静,水到渠成,所以语气很坚定,没有人能够阻拦。这样的时候有好几次,我直面危险作出选择,我发现并不是自己身上出现奇迹,变得胆大或者勇敢起来,而是对某种你视为生命的事业的不可改变的追求和热爱所致。
当你热爱(不是追逐)某种事业,你就会全心全意地投入,毫无保留地献身,就会忘记或者忽略危险,不计较代价,或者明知道有危险也无所畏惧。就像登山运动员面对珠穆朗玛峰,赛车手面对生死时速,冲浪者面对惊涛骇浪,即使金三角硝烟滚滚风云变幻,对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中国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挖掘一座文学金矿,不,简直是一座宝藏更具有诱惑和挑战呢?
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一切忘我皆源于激情和献身精神。军人热爱战场,所以面对枪林弹雨无所畏惧,爱国者热爱祖国,所以对侵略者决不屈服,爱情使人生美丽灿烂,所以才有人以身殉情。我热爱文学,因了这热爱我别无选择,同样因了这热爱我才有了独自走进金三角的奇特经历。
补充一句,回程途中遇短暂飞机险情,我险些没有心脏病发作晕死过去。
金三角,美丽的金三角!
如果不是贫困、疾病、战争、毒品、暴力和罪恶困扰着这片美丽如画的原始土地,它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具开发价值的旅游胜地。那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令人眼花缭乱的珍禽异兽,雄伟而奇异的山川河谷,还有神秘动人的风土人情、民族部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都是人类世界不可多得的最后遗产……
我从美斯乐前往孟萨采访途中,在一处地名叫做中寨的地方,时值下午,太阳已经偏西,突然一片云彩涌来将阳光遮挡。我抬头一看,天空如洗,哪来什么白云?分明是成千上万的鹭鸶和白鹤在天空快乐地翱翔。我是城市人,打我记事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数量如此之多的白鸟,它们像圣洁的雪片,像传说中上帝的天使,像我小时候读过的童话故事中美丽的精灵在天上翩翩起舞,它们不停洒下细碎而快乐的叫声填满我的心房。太阳斜斜地透下来,天空因了它们而变得无比生动,无比美妙,我像走进一个纯洁的梦境,走进一个真正充满高尚一尘不染的童话世界。我流下眼泪,不是为悲痛而是为美丽而哭泣,是为我们这个世界至今还保留的一片美好圣境,一块能让我们心灵安静憩息的神圣净土而感动得热泪滚滚。
朋友说:这是金三角有名的鸟国,像这样规模的天然鸟国还有几处。
哦,鸟儿,美丽的鸟儿,你们快乐地飞翔吧,但愿人类的罪恶不要干扰你们最后的舞蹈。我在心中默默祝愿。
但是一年多后我接到朋友来信,他说由于修公路发生山火,我们到过的那个鸟国已经不复存在。一连数日,我伤心难眠。
在金三角,我有幸见过一次野象群,那是在马鹿塘采访的日子,一天清晨,我偶尔发现村子对面的山坡上有许多移动的幢幢黑影,我怀疑自己看差了眼,连忙取出望远镜来。我的天!那是一群大大小小的亚洲野象,约有十几头,正甩着鼻子和尾巴,悠然自得地从树林里走出来,绕过村子边缘,这仿佛是一种古老的约定,与人类友好相处,互不侵犯,所以身躯庞大的它们丝毫没有侵犯人类的意思,又慢慢走进对面的山箐,消失在黑黝黝的树林世界里。
我内心感动无以复加。是谁背信弃义,撕毁古老约定,疯狂侵略动物家园,大肆滥杀珍禽异兽?是我们人类!是罪恶的人类!在金三角,尚存大约十万平方公里热带雨林无人区,这是地球上仅存不多的动植物基因宝库之一。但是我从有关方面获悉,近年来由于毒品犯罪呈现内敛之势,许多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当地民族“罂粟部落”都向无人区深处迁移,他们毁林开荒,烧山烧林,日趋破坏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更由于国际社会对毒品犯罪打击力度加大,一些毒贩将走私犯罪的贪婪目光又盯上野生动物,于是数量稀少的亚洲虎、亚洲野象、金丝猴、马来熊、黑猩猩、白孔雀等等成为罪恶枪口的牺牲品。仅中国云南海关1999年多次查获从金三角偷运入境的珍贵动物皮毛数以千计……
惊心动魄!罪大恶极!
2
金三角,苦难的金三角!
自从1950年国民党军队闯入这片原始而寂寞的土地,如同一个古老的魔盒被上帝之手打开,没有飞出象征吉祥幸福的和平鸽,也没有象征财富的金羊毛和金剪子,而是站起一个面目狰狞的黑色妖魔——毒品王国。
自此金三角年年战争,苦难重重,战争和毒品的烟雾笼罩在这片美丽土地的上空再也没有消散。罪恶的痕迹好像一道道丑恶的疮疤涂抹在金三角大地上,就像那些原本纯净的心灵被打下无数丑陋的烙印。我不禁要问:金三角,这个人类的世纪噩梦,你究竟还要狰狞多久?
一个掸邦头人对我说:如果我们不种大烟,我们拿什么东西换回我们需要的盐巴、酒精、布匹、煤油、火药、子弹、农具、百货和日用品呢?那时候连马帮也不会进山来,因为他们只会空手而归。
在另外一个比较靠近公路的寨子,本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投入资金帮助当地人开发和种植经济类作物,以替代罂粟的经济效益。第一年种植草莓,建了塑料大棚,实验结果很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山坡太陡,气温太高,旱季太干,雨季又太多雨水,大面积推广注定不能取得成功。
第二年改种大白菜,一年两季,获得丰收。问题是丰收的大白菜堆积如山,没有公路,靠什么驮运?如果靠人背马驮,再经公路铁路水路运进城市,大白菜就变成黄金价。所以大白菜只好全都烂在山里,变成蚊虫飞舞的生态污染源。
后来尝试种植甘蔗。泰国、老挝、缅甸相继同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合同,在金三角以及周边新建若干糖厂,以引导当地居民搞替代种植,增加经济效益。许多原来种植鸦片的坝子和交通方便的地方,碧绿的甘蔗林取代了姹紫嫣红的罂粟花,一车车滚滚而来的白糖以及甘蔗副产品酒精、化肥等等取代了黑糊糊的鸦片和海洛因。联合国有关组织1998年发布公告说,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大约缩减五分之一,是近十年中毒品种植面积最低的一年。
种植甘蔗毕竟只是有效努力之一,一个困难的前提是,运输沉甸甸的甘蔗需要公路,需要交通条件,所以这项改革措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难以在金三角更加广大的山区腹地推广。[奇书网-wWw.QiSuu.cOm]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缉毒官员说:由于高科技的引入,毒品犯罪更加隐蔽化,各种新型类别的毒品层出不穷。同五六十年代庞大的鸦片走私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就是同七八十年代的粉状海洛因相比,也已经今非昔比。比如冰毒、药水、药丸,毒贩将毒品精制成各种体积小重量轻的成品,从前需要一支庞大的马帮才能驮运的沉重鸦片,如今变成体积小重量轻的药丸,一匹马就能轻易带走。仅1998年底泰国政府发布缉毒通告,在金三角南部的泰缅边境一次就缴获毒品(药丸)高达二百三十万粒!
世纪之交的公元2000年,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传来,据美国国务院公布数字,1999年金三角生产鸦片较上年减少百分之六十二,呈递减趋势。而一个从前并不生产鸦片的穆斯林国家阿富汗却异军突起,首次超过金三角成为世界上新的鸦片王国。
毒品的魔影没有远去,它仍在威胁整个人类,但是人类社会毕竟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毒品的未来,走向文明的大同世界。我相信金三角也将缓慢而艰难地走出历史和毒品的阴影,只是这个过程充满艰辛,充满流血冲突和无法避免的牺牲……
3
公元1992年,一条新闻传遍全世界:金三角汉人自卫队也就是前国民党残军,终于向泰国政府交出全部作战武器。至此,从1950年李国辉兵败大陆算起,这支创造金三角神话的汉人军队终于正式解体,变成真正的和平居民,而金三角泰国境内多达近百座的汉人难民村不再拥有合法武装,成为名副其实的和平村。
如今的美斯乐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宁静的难民村。
远远望去,群山环抱之中,黛色树林如波浪起伏,一碧如洗的蓝天之下,一座金碧辉煌的佛教寺院如极乐世界高高矗立。这座佛寺为当今泰王九世的母亲,也就是皇太后亲自捐赠给美斯乐居民的,以示皇恩浩荡,如沐春风。佛教乃泰国国教,因此这个举动也可以看做仁慈的皇室对于这些归顺政府的汉人难民一种特殊恩典,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寓意不可谓不深长。你们既然归顺政府,就不能再信仰什么三民主义,你们必须皈依佛教。归顺不仅要归身,还要皈心。所以如今这座佛寺就成了难民村的精神和政治象征,每逢政府规定的宗教节日,佛寺里人头攒动,一派香火旺盛的可喜景象。
1992年之后,美斯乐逐渐向外界开放,准确说是搞活旅游经济,利用金三角的名声赚钱。于是在那座圆弧形巨大金佛塔俯瞰之下,我曾经独自下榻的美斯乐丽所,从前杀气腾腾的反共抗俄训练班旧址变成一座花团锦簇的山林公园,公园四周修起宽敞的回廊,有许多摊点出售旅游纪念品和当地土产。我有时爱到公园徜徉,因为是雨季,少有观光客,所以我这个外人很快就与摊主熟悉了。摊主无一例外都是女人,有老太太,抱孩子的大嫂,也有花季少女,绝没有一个男人,连一个白发或者秃头的老男人也没有。我从这里经过她们便招呼我,拉我看这看那,总之很热情执著地劝我买她们的东西。
她们的货物相当单调,基本上千篇一律,没有什么特产,说明此地旅游经济刚刚起步。我看见除茶叶、干菌和木耳是当地货外,一些标明玉石但天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石头(当地不产玉),其余货物多为大陆舶来品,有药品、食品、百货等等,如红花油、风油精、娃哈哈、男宝女宝之类,居然还有一朵来自峨嵋山的干灵芝!我指着灵芝问她们,这是从峨嵋山来的吗?摊主是个抱孩子的大嫂,三十多岁年纪,她向我保证说是从峨嵋山进的货。我笑了,说:“你去过峨嵋山吗?告诉你,峨嵋山早就没有灵芝了。”大嫂就装出生气的样子骂道:“你这个台湾鬼佬!这朵灵芝就卖给你家了,你家不买就不放你走人!”
金三角民风淳朴,一人做生意,别人也不抢道,都围在一起做说客。她们管台湾人叫“台湾佬”,香港人叫“香港仔”,日本人叫“小鬼子”,惟独对大陆人没有称呼,因为大陆游客基本上是个空白。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台湾佬?”她们一伙女人就嘻嘻哈哈地笑,说:“你家不是台湾佬?嘿,看你家的衣服,还想骗人!”那天我穿了一件在台湾桃园机场买的T恤衫,上面印有台湾机场字样,所以她们便认定我是台湾佬无疑。她们对台湾佬的好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金三角,许多难民村随处可见各种牌匾,上书某某学校、某某道路、某某建筑或者某某公共场所,为台湾某某捐建字样。连清莱到美斯乐的山区公路都是由台湾慈善公会捐建的。另外台湾每年都要拨给难民村一定数量的名额,选拔学习成绩优秀的中学生到台湾免费读大学,这也是汉人后代走出大山,走向文明社会的一个机会。
我说:“你们错了,我真的不是台湾佬,我从大陆来的。”她们停止说笑,个个都很惊奇,互相看看,脸上写满疑问。我就掏出护照让她们看,她们叽叽喳喳地传看,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识汉字。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大约识一点汉字,但是她好像不大认识简体汉字,偏着头看了半天,然后不服气地说:“你家从大陆来?大陆哪个省,哪个县?”我知道她们百分之九十以上祖籍都是云南人,就存心跟她们开玩笑说:“我从云南来。云南省成都市。”
她们全体发出“啊嘎——”一阵惊叫,然后惊讶和兴奋之情就久久地停留在脸上。几个人同时争着告诉我,她们也是大陆人,老家都在云南。我发现她们对“云南成都”的错误毫无察觉,就装作对她们来历一无所知,故意问她们都是云南什么地方人?哪个地区,哪个县?回去过没有?她们显出茫然的样子,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回答她们应该是云南什么地区,什么县,哪个村子人氏。当然更没有人回过老家。
我装出不相信的样子,说你们都是假云南人,连云南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说话口音也不对头。那个年轻女孩子委屈地分辩说,“那是我爷爷的老家,连我父亲都没有回去过。但是你家听听,我们说的可都是真正的云南话啊。”我笑着纠正说,“你们说的哪里是云南话,是金三角话。”她们全都不服气,齐声说:“你家说给我们听听,哪样才是真正的云南话?”
准确说,金三角汉话比较接近滇西话,它实在是一种很好听的,发音软软的(云南话音调较硬),明显带有混杂口音的华侨语言。记得我在边疆当知青,农场人来自天南海北,所以农场出生的下一代就讲一种不同于任何云南地方话的“农场话”。我认为金三角的汉话有一点像农场话,也与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华语相似,没有云南地方腔,却有云南调,因此更像一种云南普通话。因为我通常与她们讲的是普通话,所以她们并没有真正听过我的口音,现在她们一齐噤了声,眼巴巴地望着我,那种迫切表情,很像一群孩子安静地等待大人讲故事。
我清清喉咙,用标准的四川话(我不会说云南话)念了一段大观楼长联,又跟她们讲了一个成都浣花溪和杜甫草堂的美丽传说。我看见她们的眼睛一个个瞪得灯泡一样大,都没有了声气,仿佛停止了呼吸。等我讲完之后,静了好一阵,才有人呼出气来。她们不断“啊嘎——”、“阿嘎——”地发出由衷惊叹,我看见她们脸上有了毫不掩饰的佩服,乱纷纷赞美道:“哇,真好听,你家才是真正的云南话!原来云南话就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却因自己这个没有恶意的小把戏感到难过,感到自责,心中漾起一种没来由的悲哀。我相信这群善良的同胞分不清家乡话并不是她们的错,她们原本是一叶远离大陆的扁舟,一片脱离大树的落叶,任凭命运的风暴刮向天涯海角。她们的后代,以至于后代的后代会不会说家乡话又有什么关系呢?
哦,我的没有根的同胞啊!
4
有人告诉我,金三角有几多,孤儿寡母多,残废男人多,公墓乱坟野狗多,等等。我深入金三角山区数百公里,沿途采访数十座村寨,所见所闻果然不谬。
连年战乱,生灵涂炭,人命如蚁蝼,如衰草,硝烟连天哭声恸,一将功成万骨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这样一幅“千村万落生荆杞”的悲惨景象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延续了两千年,然后又在金三角土地上继续了五十年。男人打仗卖命,有人收回白骨,有的人什么也没有盼回,就像渔船一去不复返,未亡人只好拖着孤儿寡母,艰难地把日子过下去。我在许多地方,接触两代甚至三代寡妇同堂的家庭并不鲜见。
战死的人,哪怕粉身碎骨,只找到一绺头发,一根白骨,也算有个交代。所以打仗人有个规矩,就是把战死者的一件东西,哪怕一片衣服碎布带回来安葬。因此作为汉人部落顽强存在的标志,就是村外山头上那些醒目而庞大的坟场。
我曾在“美斯乐之父”段希文将军豪华气派的大型墓地前流连,我也曾仔细考察雷雨田将军虚席以待的显赫归宿之地,还有许多军长师长的坟墓,这些墓地不仅如愿以偿地留住了主人生前的地位、权势和无限风光,而且也生动形象地昭示部下,即使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长官也比士兵过得好。
作为鲜明对比,那些长眠山头的士兵土坟就不大美观,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塌的塌,陷的陷,有的地方挤作一团,有的地方又稀稀疏疏,由于无人管理荒草疯长,连那些墓碑也都歪歪倒倒。有的还有一块石头墓碑,上面刻几个汉字,注名生辰年月,姓氏籍贯等等,有的干脆没有墓碑,也没有名字,也许只有他们活着的亲人记得他们的最后归宿。
这样豪华与简陋,显赫与无名的坟场墓地在每一个金三角难民村比比皆是,至于总数到底有多少,几百处还是几千处,总之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它们的确切数目。我认为即使弄明白也没有太大意义,活着的人还没有脱离苦海,你就算把死人弄明白又能怎么样呢?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念头在乱坟间到处游荡的。
当时有向导小米陪同,但是他是个相信风水的人,对我坚持要去坟地考察很有意见,认为这是一个将给他的年轻人生带来晦气和背运的倒霉建议,他想不通我为什么偏偏喜欢上那种地方,而一个大活人上那种地方乱逛有什么意义?难道准备把自己跟他们埋在一起不(奇*书*网-整*理*提*供)成?所以他就一个人远远躲在公路上等我。我这人不大信鬼神,所以也就不怕晦气,我之所以坚持要来坟地,是因为我想亲眼看一看,那些长眠地下的原国民党残军官兵都保留什么样的心情。
我看见军官依旧扬眉吐气飞扬跋扈,士兵窝窝囊囊愁眉苦脸,他们即使到了地下也不能混为一谈。我在泰缅边境一座著名的桂河大桥(二十世纪经典战争片《桂河大桥》即以此为题材)盟军阵亡者墓地,看见数以千计的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阵亡官兵的墓碑,他们从上校到列兵,每人占有相同面积(大约一个平方)墓地,一块完全相同的铸铜墓碑,上面铭刻各人的国籍、姓名、出生年月、军队番号和军阶职务。那是一种和谐地体现西方人即使到天国也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不搞特权,你在人间握有再大权力,享有再崇高威望,即使你是万人之尊的将军,都被时光无情地留在了过去。到了天国,站在上帝面前的你我他同样一无所有,只剩一颗被剥得光溜溜的灵魂。
硝烟终于散尽,狼烟远去,昔日的战场和杀戮之地,现在正在发生改变,金三角正在恢复宁静。我仿佛看见那些长眠地下的人们,一双双饱含期待的目光穿越岁月隧道和历史风雨,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与我视线相遇。他们都是中国人,龙的子孙,永远躺在异国土地上,他们的后代在金三角继续生长繁衍,他们是根,他们的后代是树干和枝叶,这就很像移栽或者嫁接树木,最终必将结出另一种果实。我觉得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物种进化和不被淘汰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适应环境。
树根们在地下沉默。
我觉得他们似乎还在期待什么,或者他们还想表达什么,但是坟地一片沉寂。我在广大无边的静谧中遨游,似觉冥冥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它不是声音,也不是文字、图像或者形体,而是一种气,一种感应,一种磁场。它不是物质的,因为物质无法穿越两个世界的界限,所以它一定是非物质的,类似意念、精气、灵魂之类,这些神秘的东西包围我,而我完全是凭着第六感官,也就是灵感才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我开始进入一个非物质世界!
我感到自己不可思议。我想我这个自称无神论者的人可能疯了,至少精神出了毛病,因为坟地上空无一人,我怎么可能与死者对话呢?或者说就是死人发出什么密码信息,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静谧像渐渐凝固的冰块,寒气压迫着我的神经,我感觉一个东西离我越来越近,我无法看见它,但是我分明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像你觉得身后有人,一回头却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一样。你没有看见什么并不等于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我的新发现,我总觉得自己快要接近一个东西,伸手就要捉住它,然而它总是像空气和水一样从我手缝中溜掉,差之毫厘,失之交臂。于是我苦恼万分,灵魂苦苦挣扎。意念之手无边无际,若有若无,佛说,大道如天,大化无形,我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这时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脚步不是来自天空大地,而是来自我的内心深处!
我疑惑地放眼四顾,一轮辉煌的夕阳正像一艘庞大的航空母舰慢慢燃烧西沉,在我身后,金三角重重叠叠的山峦在夕阳余辉中灿烂燃烧。我看见北方的大山峡谷之中,一条汹涌澎湃的著名大河在岁月激流中渐渐冷却凝固,它的形状像一条中国的龙图腾,龙的上半段在中国,叫澜沧江,下半段横贯南部亚洲,名字叫湄公河。而我脚下,就是那些不幸灵魂的栖息之地,远远的山坡有条通往美斯乐的空无一人的公路。
座南面北!面北……
一瞬间,我忽然大彻大悟,灵魂出窍,夏雪冬雷,石破天惊。我的全部灵魂与那个游荡的历史意念迎面相撞,就像宇宙飞船和太空舱对接。
我轰然爆炸!
请跟我来读懂那群流浪的中国人吧!他们长眠在地下,这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无论他们生前做过什么,当兵打仗,离乡背井,抗日战争,反攻大陆,走私贩毒,龙蛇争霸,你争我斗,效忠朝廷,他们死后都亲热地拥挤在一起,背向金三角,背向异域和陌生的印度洋,他们与我目光交织,那是何等热切和期盼的生动目光!于是我明白了,在我脚下这片土地上,一群漂泊无根的中国人,他们永远面向北方,那是他们共同的祖国和家乡,是他们魂灵和精神向往的归宿之地!
哦,北方!我的永远的……北方啊!
我想起一部曾经感动无数中国观众的日本影片《望乡》。妓女葬身南洋,但是她们全部背向北方,因为她们日思夜想的日本国已经抛弃她们。而这群离乡背井的中国人,他们却个个面向祖国,至死不渝!
1998年秋天,我在金三角看到的这一幕不是电影,不是艺术造型而是一个令我肝胆俱裂的真实场面,数以千百计的坟墓,一律整齐地面向北方,面向祖国!这是一个何等惊天地恸鬼神的感人场面啊!后来我陆续考察段希文墓,雷雨田墓,各处汉人难民村墓地,居然全部惊人地一模一样,无一例外者!他们全都面向祖国和家乡,长跪不起!
这时我的眼泪再次汹涌而出,泪洒滂沱。是的,人可以死,尸体可以腐烂,墓碑可以剥落,名字也可以遗忘,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与祖先血脉相连,敬畏永存。有这分思念,这种姿势,这种永不改变的炎黄子孙对故国故土的感激之情就足够了,他们长眠金三角,但他们永远是中国人。
我伏身而跪,向死者,向我魂牵梦萦的同胞之魂,重重磕了三个头。
5
小米见我走上公路神情有些恍惚,就紧张地问我:“看见什么了吗?”
我说:“他们……回家了。”
小米说:“他们是谁?”
我改口说:“哦……应该是我们,走吧。”
一周之后,我返回中国大陆。
1998年10月1日—1999年7月5日初稿
2000年5月 四稿改定 7119509
后 记
当我已经从金三角返回国内,一些朋友陆续得知我独自深入金三角的消息,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责备我:你为什么要到那样的地方去?你不怕死吗?
朋友的关心令我感动。我肯定是怕死的,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生活那么美好,人生那么短暂,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对未来还有那么多期待,我怎么愿意去死呢?如果我不幸死了,我到金三角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从来不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甚至算不上一个勇敢的人。我天生胆子小,有恐高症,晕血症,惧怕开刀,从不敢玩“蹦极”、“过山车”之类勇敢者游戏。如果乘飞机在高空遇强气流,每次我都会因为恐惧而紧张得身体颤抖冷汗涔涔,我不能想象如果飞机掉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模样。同样的恐惧还发生在几次身体不适时,我疑神疑鬼觉得自己患上什么不治之症,绝望得好像判了死刑。
小时候我常问自己,如果你上了战场会是个好士兵吗?如果你被敌人抓住严刑拷打能挺得住吗?上述问题我从来不敢深想,因为答案藏在心里,它分明使得我心情沮丧,对自己评价失去信心。
问题是1998年夏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进入金三角采访,我对危险完全不屑一顾,勇往直前,藐视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这不是说我变得勇敢起来,而是因为我浑身燃烧着激情、向往和冲动。
当满星叠发生枪战打死好几个人时,当地朋友都阻拦我前往,我并不是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危险,死亡实在是个很短暂的过程,一旦发生便不可更改。但是我还是被巨大的好奇心、职业的采访欲望和对写作的热爱所驱使,对我来说,那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好比飞蛾扑火,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所畏惧。我对朋友讲,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就是丢掉性命我也决不后悔。我奇怪自己作出这个决定很冷静,水到渠成,所以语气很坚定,没有人能够阻拦。这样的时候有好几次,我直面危险作出选择,我发现并不是自己身上出现奇迹,变得胆大或者勇敢起来,而是对某种你视为生命的事业的不可改变的追求和热爱所致。
当你热爱(不是追逐)某种事业,你就会全心全意地投入,毫无保留地献身,就会忘记或者忽略危险,不计较代价,或者明知道有危险也无所畏惧。就像登山运动员面对珠穆朗玛峰,赛车手面对生死时速,冲浪者面对惊涛骇浪,即使金三角硝烟滚滚风云变幻,对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中国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挖掘一座文学金矿,不,简直是一座宝藏更具有诱惑和挑战呢?
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一切忘我皆源于激情和献身精神。军人热爱战场,所以面对枪林弹雨无所畏惧,爱国者热爱祖国,所以对侵略者决不屈服,爱情使人生美丽灿烂,所以才有人以身殉情。我热爱文学,因了这热爱我别无选择,同样因了这热爱我才有了独自走进金三角的奇特经历。
补充一句,回程途中遇短暂飞机险情,我险些没有心脏病发作晕死过去。